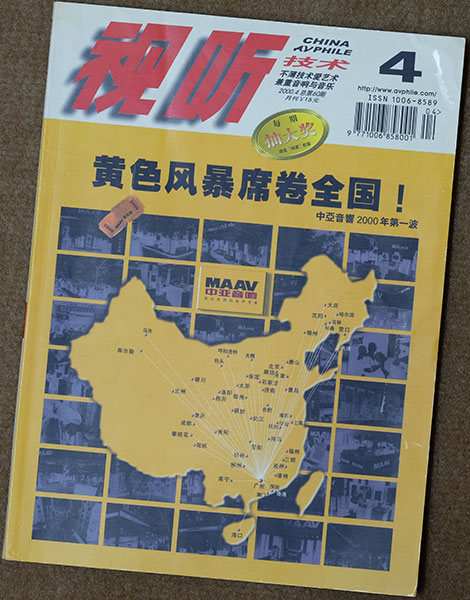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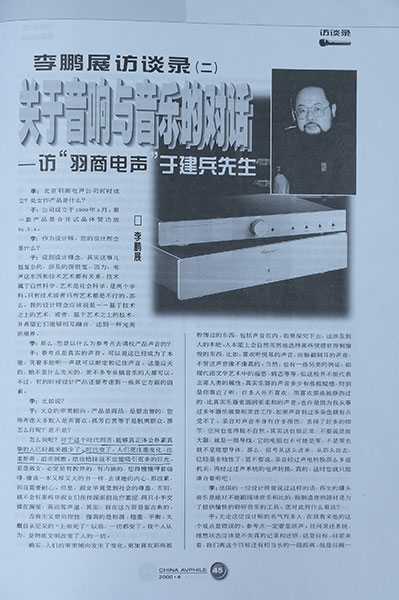
文/图 李鹏展
李:北京羽商电声公司何时成立的?其处女作产品是什么?
于:公司成立于1995年5月。第一款产品是合并式晶体管功放 №6.4。
李:作为设计师,您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于:说到设计理念,其实这事儿挺复杂的,涉及的面很宽,因为电声这东西和技术艺术都有关系,技术属于自然科学,艺术属于社会科学,是两个学科。只有技术或者只有艺术都是不行的,那么我的设计理念应该说是——基于技术之上的艺术,或者基于艺术之上的技术,并希望它们能够相互融合,并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

李:您是以什么为参考点去调校产品声音的?
于:参考点是真实的声音,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了本能,凭着本能听一声就可以断定和记住声音。这是后天的,绝不是什么先天的,差不多专业搞音乐的人都可以;不过有时候设计产品还要考虑到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
李:比如说……
于:大众的审美倾向。产品是商品,是要出售的,您得考虑大多数人是否喜欢。孤芳自赏等于是脱离群众,那怎么行呢?是不是?
怎么说呢?对于这个时代而言,能够真正体会朴素真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时代变了,人们更注重变化、注重新奇、追求刺激。浓妆艳抹说不定能吸引更多的目光。若是淑女,必定是有教养的、有内涵的,您得慢慢呷着咖啡,像读一本又厚、又大的书一样,去读她的内心,那很累,而且需要耐心。但是淑女毕竟受到社会的尊重,否则就不会有那些非淑女们在传媒面前故作羞涩,两只小手交揉在胸前,燕语莺声道:其实,我在这方面还是蛮古典的。
古典广义崇尚理性,强调的是和谐、稳重、平衡。大概自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个人认为,是物质文明改变了人的一切。
确实,人们的审美倾向发生了变化,更加喜欢那些被粉饰过的东西,包括声音在内。如果深究下去,这涉及到人的本能。人本能上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那些使感官得到愉悦的东西,比如:喜欢听悦耳的声音,而躲避刺耳的声音,不管这声音像不像真的。当然,也有一些另类的例证,如现代派文学艺术中的溢恶、病态等等,但这些并不能代表正常人类的属性。真实乐器的声音多少有些粗糙感,特别是你靠近了听,许多人并不喜欢,而喜欢那些被修饰过的、比真实乐器更圆润、更柔和的声音。也许是因为我从事过多年器乐演奏和录音工作,如果声音有过多染色就有点受不了。录音对声音本身有许多损伤,丢掉了好多的细节,空间也变得极不自然。其实这也很正常,不要说是放大器了,就是一根导线,它的电阻也不可能是零,不是零也就不是理想的导体,那么信号从这头进来,从那头出去,已经是非线性了,更不要说录音经过声电转换那么多道机关,再经过还声系统的电声转换,真的,这时您就只能凑合着听吧!
李:法国的一位设计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再生的罐头音乐是绝对不能跟现场音乐相比的,我制造的音响器材是为了提供愉快的聆听音乐的工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于:无论这位设计师的名气有多大,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参考点一定要是原声。任何录-还系统,理想状态应该是不失真的记录和还原,这是目标。目前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回顾一下电声的发展历史,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仅仅是初级阶段。几百年以后,后人一定会嘲笑我们:这帮家伙,怎么这么笨!自然规律就是这样,人类的局限性使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不可能穿越时空,直到未来。
李:您的参考点是真实的声音,那么,您有没有考察一般消费群体的参考点?
于:作为一个最最普通的人,他们会自然的地以真实声音为参考点的。然而,对于真实乐器、歌喉的声音他们并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常说的“现场”,因此,这个点到什么地方参考去?
目前,我们国家的音乐普及工作还不是那么理想,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能听到现场演奏,更不要说一流的音乐厅和一流的乐团。与国内其它城市相比,北京好一些,外国的乐团、演奏家来的较多,但是北京至今还没有一所建筑声学条件具世界水平的演出场地。我们经常听的那些上榜天碟都是在那些建声条件非常好的录音棚或者是教堂里录制的。如果拿我们在国内听到的现场跟那些天碟做比较的话,这里面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另外,录音话筒拾取声音的位置也不同于我们的音乐厅听音乐会时的位置。最近,我听到日本人录制的一张发烧唱片《怒涛万里》,这张唱片拾取反射声的话筒用了三对,分为远中近放置,在声音空间处理上就比较自然,接近我们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那种空间感。
李:与您以前设计的音频放大器相比,您现在的设计在动态、瞬态、空气感、空间感等方面的表现很出色,显得活气十足,但“韵味”淡了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于:这实际上还是涉及到设计理念。 我始终认为,以目前两声道立体声而言,它应该能表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三维声音空间。在录音棚与音乐厅听音乐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在一个声环境之中,声音在你的前后上下左右,很自然的存在于空间之中;一旦变成录音,空间便被挤压变形了。我做的努力就是想在还声系统里尽可能寻找回那种空间感,当然,它与真实空间感的关系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要表现好声音的空间,就放大器而言,要有好的幅频相频特性、开环特性,闭环之后听域之外的频响曲线要尽可能的平滑宽阔。频响究竟宽到多少才好,这还要看和喇叭之间的配合会不会出问题。放大器的高频比低频难做,放大器本身的高频失真和频率特性都比中低频差。另一方面,人耳对中高频的失真要比低频的失真敏感得多。
从审美角度讲,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具有活生感的声音。有人比喻唱片是罐头音乐,那么我们何不尝试可以来点新鲜的、带着点露水、质感真切的声音呢?
至于韵味,那多半是要往声音里搓点佐料。搓兑得好可以起到遮掩缺陷的作用,弄不好,假上加假,也就是更假了。最终,我们听到的完全是与真实声音相悖的一种声音。
李:今后,您是保持目前这种设计风格呢?还是通过不同系列的产品来表现出不同的声音风貌?我个人倒是很希望您能有一个系列的或某一款产品能保持“古典”一点的声音,因为您毕竟有一个搞过艺术的文化背景。
于:搞过艺术的人就一定要古典吗?那么没有搞过文化艺术的人就很现代?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在说,古典等于文化。这是个概念理解问题。现代也是文化,但时尚不一定是文化,二百年后,我们这个时代就成了古典了。
在不同系列的产品里我肯定要考虑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文化层次、审美趣味等等因素。
李:您对主观听音评价与客观技术指标的关系怎么看?
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目前我们所能够确定对声音品质有关键影响的技术指标还不是太多,有一些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还没有统一,技术指标与主观听音评价之间的关系还不能对应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主观听音发现的问题在技术指标上得不到完美准确的诠释。两部技术指标完全相同的机器,有一部很好听,另一部就很难听,这是常见的事。对于谐波失真,目前只标总谐波失真,而没有标出是奇次还是偶次的,而奇次与偶次谐波失真在听感会造成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国外的某些放大器特别标出了三次谐波失真。虽然偶次谐波会使声音变松变软,但是也不能过多的增加它,否则声音会变得缺少力度、缺少个性。事实上,在主观听音中所发现的声音变化与差异,都说明还声系统中的物理参量在发生变化。另外,在主观听音评价中所发现的这些暂时还不能用技术指标来诠释的差异与问题,我想就权且叫它“指标外的指标”吧。随着我们对物质世界不断深入的认识,最终,人类对此一定可以有更多更深的把握。
目前,我们业界要写在产品说明书里的三大指标,充其量只是对产品最基本的界定,也就是告诉大家:别太离谱了。
另外,我想谈谈对主观听音评价的一点看法:我认为,现在规范的那十几对评价用术语,还远远不能涵盖其全部内容,特别是心理方面的。主观听音评价研究应该重视一下美学方面的内容,因为听音本身也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李:您主观听音时常用的软件有哪些?
于:分为几组吧:小提琴、大提琴,小型室内乐、钢琴、人声(特别是女声和童声)、大动态的交响乐、打击乐等等。比如小提琴我经常用Paganini的二十四首随想曲,大提琴则是Starker演奏的Kodaly,这两张唱片都是无伴奏的。校声用的唱片最好是真实乐器类的,不要用合成器音乐或者流行音乐,因为这些音乐制作的成分太大,不太容易找到参考点。还有,不要用太老的录音校声,它本身录的就不好,而你非要把它播好,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李:您校声时掌握的原则或技巧是什么?比较注重音色,还是平衡性,或者其它?
于:校声是对设计的调整和补充,籍以希望声音向着既定的目标接近,也是设计的一部分。我校声的原则也就是我对声音的追求,也包含着我们前面说过的设计理念。
对于声音,人耳最敏感的东西是音色,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音色做好。接下来就是平衡度,定位、空间、声场等等。还要考虑到把各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负面的正面的,减掉哪些增加哪些,拿捏到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枯的恰到好处的境界。
校声过程中常常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能正确的判断声音的对否,二是判断出来又没有技术上的办法改变声音。对于前者,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艺术上、听音训练方面加强煅练,而对于后者相对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对于模拟音频放大电路而言,其电路基本形式几乎大同小异,同样一个电路,同样的元器件,如果十个工程师去实施成产品的话,那么,会得出十种声音。这中间,显然是经验和侧重点起了作用。这个经验中包括了相当多的东西,像电路结构、工艺结构、布线、元器件、电路参数设置等等。这就要求设计师有丰富的经验积累,深厚的技术功底,改变电路的哪个方面声音会朝着什么方向走,做到心中有数。一个成熟的设计师设计的系列产品,往往能保持着比较相近的声音倾向,这也就说明这个设计师具备了驾驭声音的能力。
对于电路设计而言,不同的电路结构,不同的电路参数都会带来不同的电路性能与声音倾向。一个音频放大器差不多要有一百到三百多个元器件,应该说,每个元器件都是声音的可变因素,关键看你去怎么搭配。设计师这活儿,设计也好,校声也罢,都有点象画画的,给你一块白布一堆色彩,画去吧。赤橙黄绿青蓝紫爱怎么搭配都是你自己的事了,至于构图好不好,色彩协不协调那就是看画人的事了。设计,这里面充满着创作的成分,创作的激情。
李:您心目中的经典产品有哪些?
于:胆机中有Marantz、Mcintosh、Matisse。直到今天,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声音表现上,这些机器仍然是佼佼者。晶体机中有Mark Levinson早期的产品,Cell、YBA等等。这些机器都有着一种不俗的声音追求,那种追求不仅仅是用富有音乐感这样的字眼可以概括的,那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气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一些中小功率机器,电路很简单,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元器件也很一般。有个别机器的电路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两级电压放大只用了四只晶体管,包括输入差分放大和温度补偿,甚至还带自举电路,也就是正反馈。今天看来,您说,这样的机器能听吗?但是,声音真的是说的过去。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谈过的一些问题,这些个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和思考。普遍的讲,日本的机器,工艺很棒,技术上也有许多商业上的卖点,但是,他们的声音总缺少那么一种气质、一种追求,这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我与日本录音界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日本人在工作上非常认真努力,但是他们缺少才华和灵气。
李:您对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怎么看?
于:技术是基础,如果没有技术,一切都是空谈。做个比喻:我觉着帕尔曼的琴拉的不好,我的境界比他高,我的音乐感比他好,可是我没有帕尔曼的技术,我拉不出来。对于电声而言,如果只有技术,而不具备应有的文化艺术修养,只能是一个匠人。所以,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辩证的。
电声设计确实需要设计师有起码的音乐艺术修养、鉴赏品味,它是衡量设计师整体水准的一部分,这个关系很直接的,和其他科学不一样,设计师最终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判断取舍。事实上,文化艺术对于其它门类的科学家也同样重要。当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美国人看到,研制这些人造卫星的苏联科学家的艺术修养普遍高于他们。也许艺术对于科学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但是,艺术的思维是形象的,它能够启发人的想象力。另外,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创造性,任何一种艺术都要求是个性的创造,这就为科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更宽亮的窗口,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李:国产音响工业的现状、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于: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看,我国的音响工业尚处在上升时期和初级阶段,部分企业存在着短期行为,抄一把就撤。由于这种心态,再加上国企的不景气,至使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许多元器件必须依赖进口,处于被动状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资本、就是价值。如果我们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上徘徊,那么,我们可以成为音响产量大国,但成不了世界水平的音响大国。
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常常和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自尊的、民族的,以及几百年来在国人心中的压抑感。所以,我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工业的兴衰注入了极大的关注,希望它能繁荣昌盛。但是,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不怕未来的路有多么的遥远,眼下,却因为鞋子挤脚而寸步难行。
李:那么,您认为国产音响业与外国音响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于:差距是多方面的,整体的。做这样一个设想:也许我们在某个方面拥有了世界的顶尖技术,而与之配套的方方面面却一塌糊涂,这样的组合能代表一种水平? 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人是第一位的,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决非空话一句!
还有一点题外的话,那就是:在电子领域里,较其他行业,音响业的发展比较缓慢,特别是对于提高音质重播以及心理声学、人类听觉与精神反映等方面。从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放大器件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而第一代的电子管在音响领域仍然有着它自己的价值,这很有讽刺意味。我个人认为,电声技术若出现质的飞跃,必须是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那时,我们可以彻底否定现在。现阶段,基本上是小打小闹,无非是您的声音甜一点,他的松一点,您的亮一点,他的软一点。
李:您对器材搭配怎么看?
于:搭配很重要,好了事半功倍,差了功倍事半。搭配说透了是把器材的物理特性重新加以组合,多少带点创作的意味。关键是扬长避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究竟什么样的平衡才是最佳,这有点因人而异,既使是我帮您调理的系统您可能也不怎么满意,这涉及到音响美学的一些问题。
李:您是怎样看待家庭影院的?是AV最终取代Hi-Fi,还是AV与Hi-Fi各有各的发展归宿?或最终的归宿是Hi-Fi?
于:AV与Hi-Fi完全是两回事,谁也代替不了谁。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将来没准会出现那种两者兼顾的音视频制式。
在人类感官所摄取外界信息的比例上,视觉占的比重最大,约百分之七十几,而听觉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说,人聋了比瞎了幸运,聋子可以凭眼睛看明白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而瞎子就比较麻烦。也因为感官的一系列属性,所以,人类在凭视觉分辩事物的时候可以不怎么动脑子,而使用听觉的时候则常常要全神贯注,并且进行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电视看的越多,人却越来越傻的原因。当然,如果把人类感知信息的器官都调动起来,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触觉的,那么,将会获得身心上的极大满足。
我希望朋友们能多听听Hi-Fi音响,听听古典音乐。今天的世界,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刺激,神经已经变的越来越麻木,这似乎并不太人性。我希望我们人类回到大自然当中,回到人性的和谐之中,感受美感受情感,感受一切属于我们人类的东西。
1999-10-30
此文章已在成都《视听技术》杂志
2000年第四期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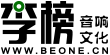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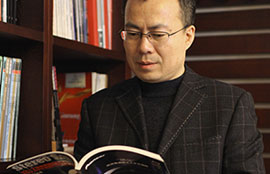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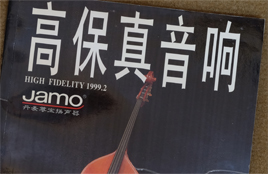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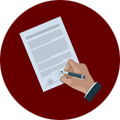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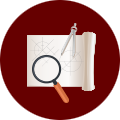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41041102000145号
豫公网安备41041102000145号